
村上春树《边境 近境》的中国书写(2)
村上春树《边境 近境》的中国书写(2)
二、村上春树的中国嫌恶
在纪行文集《边境.近境》中,除了写到中国之旅,还书写了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旅游体验。譬如,美国那幽静的写作圣地东汉普顿,给他一种“享受”;日本山口县的乌鸦岛,虽让他遭遇到种种苦难,但他感受到那无人岛的“奥妙无穷”;横穿墨西哥时,虽说交通不便并有着动乱余波,但他认定那是个“非常吸引人的地方,迟早还想去一次”;在赞歧乌冬面之旅中,他为香川人对乌冬面的温情孕育出的美味而感动;而驱车横穿美国大陆,虽说一路极度无聊,但最后到达西海岸时难掩内心激动,并因旅程能够如此之长而发出美国果真是大国的感慨;最后一篇是他走进了故乡神户,因阪神大地震后的神户变化很大,让他不知自己身置何处,但那种变化在作者看来是神户“持续地处于暴力的阴影之中”,这毕竟对母国将来走向的担忧,可以说是一种爱国心与善意的表现。在这部《边境.近镜》纪行文集中,唯一流露出对其厌恶与蔑视的,就是村上春树在去往诺门罕遗址的途中所见到的中国。他是“极端的中华料理过敏分子”,声称对“中华料理”一概不吃,他的这次中国游历在饮食上的苦不堪言自不待说。而他的中国嫌恶更具体地体现于他在东北几座城市的“行”与“住”上。
1
中国的“行”
首先,村上充分展现了中国交通工具的落后与不便。对中国硬座车他的体验如下:“从大连开始被塞进挤得连厕所都去不成的、堪称中国式混乱极致的满员‘硬座’车(原本计划乘飞机去长春,但航班被无甚理由地取消了,突然改乘火车),摇晃了一夜十二小时,累得一塌糊涂。到达长春站时,觉得脑浆组织也好像随同周围汹涌澎湃的情景而大面积重组一遍”[2]119。而村上春树在从长春坐硬座火车去往哈尔滨的途中,又因对面男子开了车窗再没关上,致使窗外异物飞入村上的眼睛,他在文中这样描述:“那时我还是中国旅行的初学者,不知道不可对着车行方向而坐这个铁的守则。中国人满不在乎地从窗口扔所有东西,若开窗坐在窗边,有时会遭遇意料不到的灾难。啤酒瓶啦橘子皮啦痰啦鼻涕啦,各种各样物件从窗外嗖嗖飞过,弄不好很可能受伤,下场更凄惨亦未可知。仅仅异物入眼或许还算幸运的。”[2]126读到这里便会忍俊不禁,虽然作者的表述有些夸张,但这确实在中国八九十年代绿皮火车上有过的现象,一旦不幸与车外飞来的脏物或硬物“亲密接触”,估计要比20年代作家芥川龙之介在中国目睹的浔阳江上的大便、湖心亭畔的小便与京剧名伶的鼻涕等感到痛苦多了。
村上春树从哈尔滨去往海拉尔,乘坐了当时中国列车中最高档的“软卧”。虽然他说不再像坐硬座那样去厕所时被人抢走座位,也没有小孩子在地板上撒尿,但他还是有不满之处,一是嫌弃卧铺枕头花花绿绿,不够卫生;二是在软卧室内与一位少妇同乘,有点别扭。再有就是“厕所照旧近乎崩溃状态”。而从海拉尔到新巴尔虎左旗,村上春树又坐了约四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因为道路是从茫无边际的草原穿过的坏路,一路颠簸,而当地司机早已是轻车熟路,以七十公里左右的时速驱使长途汽车风驰电掣,文中写到:“总的说来坑洼躲得确实巧妙,但有时没躲好,致使脑袋‘呯’一声撞在窗上,或险些咬掉舌头。”[2]137村上春树再次用其幽默笔调,书写出他在中国之旅中饱尝了交通工具落后与不便之苦。
其次,极度刻画了交通状况的混乱与隐患。村上春树对中国的交通混乱与拥挤状况颇有微词。他说:“路况差得接近极限,车自行其事地行驶,人自行其事地行走。我花了好些时间才跟上其步调,或者不如说直到最后也没跟上。这以前我在罗马、伊斯坦布尔、纽约等交通相当混乱的地方也自由自在地驱车行进来着,但对于中国城市交通异乎寻常的极度混乱还是瞠目结舌,根本不想在这样的地方开什么车。”[2]121在这里,村上春树通过城市间的对比,以及使用“极限”、“极度”、“瞠目结舌”等之类的夸张词汇,道出了他对中国交通状况的种种不满。他还在文中具体指出了几件中国人的交通违规与危险事情,如四周黑下来之后车灯也不开;有人横穿马路,车也不减速,只是警告性按喇叭了事。在光天化日之下,他目睹到街上轿车和自行车相撞事故到处发生,群众卷进去争吵不止,所以他在天黑之后一步也不出宾馆。而坐火车途经牙克石车站时,村上春树不仅看到很多人不排队挤车的情景,还看到一个企图扛着自行车上火车的男子被警察逮住,并被噼里啪啦打一顿带走了。
村上春树于是对世界上的汽车公司都把中国作为唯一剩下的大型市场而虎视眈眈的经济态势感到费解。就中国当时的交通状况,他认为:“汽车数量进一步增多,那么出现的恐怕是异乎寻常的噩梦(有关中国的东西似乎都有异乎寻常的倾向),因为即使是现在这样,也足以称之为‘通常意义上的’噩梦了。然而看样子人们并没有作为噩梦来对待。由此看来,如此发展下去,势必有一天中国全境——从越南国境到万里长城——被交通堵塞、空气污染、烟头、BENETTON招牌所彻底覆盖。这或许可以称为历史必然,总之不可乐观。”[2]122这是十几年前先进国民的经验者村上春树对中国的预言,因为他感觉中国人处在“噩梦”中却不以为然,事实上中国正朝着预言的方向奔走。2001年前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于是开启了汽车消费的大幕,据相关资料显示,短短十年间中国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英赶日,跃居全球第二位。随着汽车保有量急剧增加,汽车尾气开始成为许多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据凤凰卫视报道:“中国74个城市从2013年1月1日起公布PM2.5数据,有33个城市指标超过300微克/立方米,其中京津冀最为严重。从北京到南京,以及中部的武汉,大半个中国浸泡在浓雾之中。”

2
中国的“住”
这里所谓的“住”,指村上春树在中国体验到的宾馆或招待所设施方面的状况。村上春树将外宾宿泊的中国高级宾馆视为废墟,其他旅游与观光设施被视为轻度废墟。他在文中连讽带刺的这样写道:“.我转了不少中国城市,深深觉得中国建筑师有一种能使得刚刚建成的大楼看上去浑如废墟的特异才能。例如每次进入面向外国人的高层宾馆——当然不是说全部——我们都会在那里目睹为数众多的废墟。电梯里贴的装饰板张着嘴摇摇欲坠,房间里天花板边角部位开有含义不明的空洞,浴室的阀门有一半两相分离,台灯的脖颈断裂下垂,洗面台活塞不知去向,墙壁有仿佛心理测试图的漏雨污痕。遂问:‘这是旧宾馆吗?’答曰:‘不不不,去年刚刚建成。’至于这样的才能是在何地如何产生并普及到全国的固然无从确定……”
其实,这并非是村上春树所说的那些能把新楼变废墟具有特异功能的建筑设计师的问题,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初,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新的投资项目建筑规模大,而建筑管理制度呈滞后状态,尤其是工程转包、挂靠、层层分包等现象,最终导致建造方偷工减料,唯利是图,建筑质量因此变得很差。但是,中国八九十年代面向外国人的宾馆(即涉外宾馆)在全国各地均为高档宾馆,它代表着国家形象,其设备和服务的质量都是一般旅馆不可比拟的,而且当时的涉外宾馆只准那些来中国旅游或开会的外国人入住,中国的老百姓是不可进去的,所以涉外宾馆被称为“第四世界”,对中国的普通市民来说,涉外宾馆就是高级享受的代名词,是最具现代国际水准的建筑设施。所以,村上春树笔下的涉外宾馆如此惨不忍睹,并被他视为废墟,着实是令人怀疑他描述的真实性,至少那是一种夸大,并带有一种辛辣的讽刺。
文中促使他发出“中国建筑师有一种能使得刚刚建成的大楼看上去浑如废墟的特异才能”这样感慨的,是他在参观伪满时期建造的“新京动物园”里的建筑物的时候。看到钢筋混凝土建筑物的墙壁像久经岁月洗礼了似的破旧不堪,他本来以为那是保留下来的战前建筑,但动物饲养员告知村上那是七八年前建造的,村上春树表示吃惊。为消除他的疑虑,那饲养员带他去看昔日剩下的混凝土台基,然而村上看后却不无得意地写道:“这么说自是不太合适,在我看来,较之七年前建的新混凝土墙,倒是五十年前的混凝土台基显得结实得多新得多。”[2]124同样,在海拉尔,村上春树参观了三年前建造的名为“望回楼”的瞭望台,因墙壁有了裂纹,天花板上出现一个窟窿,他认为那瞭望台“也同近年建的中国建筑物一样化为轻度废墟”。村上春树最后写道:“较之从瞭望台瞭望市容,我对观看瞭望台本身更感兴趣。”看来作为讲求质量的先进国家的国民,他感兴趣的是中国的那些“废墟”是如何造成的。
然而在新巴尔虎左旗,没有涉外宾馆,他们只好借住在解放军的招待所。村上春树在文中这样写到:“到底是军队经营的,态度冷淡得不得了,不到晚间根本没水。走廊门前五颜六色的痰盂一溜排列开去,感觉很有些像电影《巴顿·芬克》中的场景。厕所倒是冲水的,但由于水冲不下来,哪个都有大便原封不动保留着,臭味无可救药地四下弥漫。刚进建筑物时还以为进了巨大的公共厕所。”[2]136-137毕竟是在边境,条件极其艰苦,水电供应有限,因节约而导致“巨大的公共厕所”的产生,所以村上春树最后也认为“不过这怕也是理所当然的”。而新巴尔虎左旗,在村上春树看来,像是电影《原野奇侠》中的开拓者居住区,“比海拉尔还要原始、粗野”。最后到了诺门罕村,却遭受到当地蚊虫的攻击,村上诙谐地写道:“苍蝇蚊子牛虻飞蚁以及其他不知名称的长翅膀的飞虫拼死拼活围上身来,衣服上黑压压的一层。蚊子毫不客气地扎进皮肤,难受程度无法形容。再热也要扣紧帽子穿好长袖衣服和长裤,还要戴太阳镜,用毛巾围住嘴巴——若非‘全共斗’的打扮,休想在此活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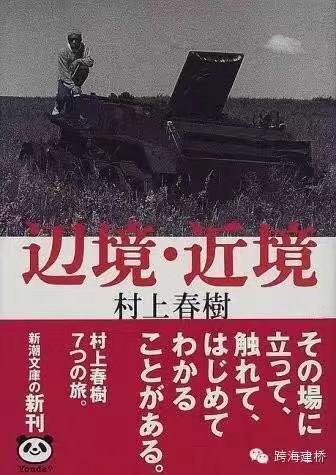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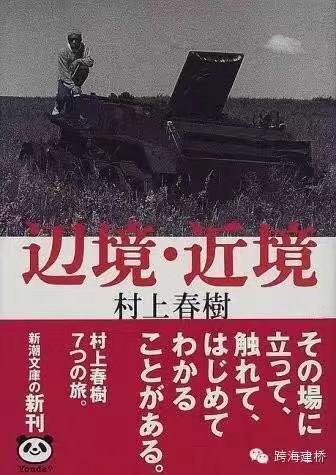
#{{item.rowno}} {{item.content}}
{{item.reg_date | date}} {{item.acc}} {{item.ref}}